
25岁以下人群,是从出生或者孩提开始,就已经被数字化设备和互联网包围的一代人。对于这样的青年,我们称之为“数字青年”。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数字青年,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。在中国,包括“北上广”在内的国际化大都市,和一线省会城市,数字青年已经逐步和全球对接;而在二三线城市,数字青年则体现出另一种特征:互联网的“亚文化”。
代际矛盾,在这一人群身上,将更为明显。而ICT技术的深层次融合,尤其是互联网应用的差异化,反而使得数字青年更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。
社交网络带来转变
对于“70后”甚至“80后”之前的人们,仍然会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模式,来获取所谓权威信息。媒体通过分析外界信息,并予以提炼,将观点输送给这一代人,换言之,信息是通过系统性的解析之后,所得的内容。
而对于现今的数字青年,社会系统很难再继续过往模式:用一个旧有的框架和认知模式,去约束他们。面对旧有框架,数字青年的第一反应,并非接受,而是质问“为什么我要接受”。
和前辈乃至前人对比,文化冲突是较为有趣的现象:当占据社会主要位置的年长者,看到新一代人,对一切都予以疑问和排斥,尤其是对前辈的信仰不予认同时,总是试图用历史来证明自我的正确性,并让年青人接受。
在互联网阶段,信息高度发达化,所有的信息和声音,都会被青年们接受,包括相互矛盾的信息和声音。解析不再是系统所能完成的,而成为个体自我解析的过程。这就是社交网络体系的互联时代。在这一时代,所有的信息都以原有姿态呈现,哪怕这些信息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抵触的,而个体则自行完成对这些信息的解析。
年青人越来越多地,不再关注官方渠道的新闻。因为,通过好友转发的内容,尤其是新闻性内容,每个人都在帮助他人进行信息过滤,同时也在接受其他人的信息过滤结果。社交网络导致信息在有同样爱好的人之间,不断回荡。这使得个体会认为,周围都是他的朋友,乃至整个社会,都跟他保持了同样的观点。通过青年们自己的沟通和传播,数字青年得到他们自己年龄段所感兴趣的内容,而对其他内容,产生了近乎屏蔽的效果。
因为所有的网络节点并未改变,这使得看似仍然自由流通的信息,已经在群体内形成了更强大的内部联接。而当内部联接很多、外部联接很少时,多数的内在信息得到了强化:和数字青年兴趣点相同的信息会被强化,让他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的;和他们兴趣点不同的信息会被弱化,并最终消失掉。
这种群体的出现,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是“极化现象”。思想的极化,是社交网络的鲜明特点。尤其当相同的人汇聚,有相同的观点形成,无论年青人还是成年人,线上还是线下,人们都更加容易选择“站队”。
在这个潮流来临之时,无论社会试图或者努力做好充分准备,都会感觉到是仓促应战,握有话语权的年长者们,已经或将会意识到,很难做好研究和应对的实践。而现实是,即便整个社会应对不足,包括数字青年在内的所有人,也仍然会被这个潮流裹挟,形成数字青年们自己的特点。
在根本上,社交网络只是工具,它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或者更悲观,只是体现了世界会加速改变这个无法逆转的趋势。
这就是社交网络的共性。这一共性将带来的转变是:当我们以为“世界是平的”的时候,世界事实上“山头林立”。
1
 相关文章
相关文章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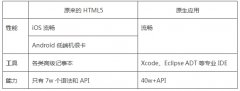
 精彩导读
精彩导读
 热门资讯
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
关注我们
